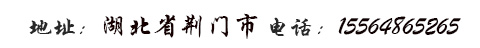异口同弦西窝羌寨走近口弦传承人王泽
|
白癜风诊疗经验 http://baidianfeng.39.net/qzzt/bdfzlff/ 口 弦 在羌族民俗文化保存较为良好的北川羌族自治县青片乡上五村,我们走访了三位口弦文化的传承人——王泽兰、周顺兰和赵永珍。通过听老人讲故事,我们希望口弦这一文化遗产,不再局限于网络的搜索、刻板的描述,而是与她们 的人生融为一体,与这片与众不同的土地血脉相通。请跟随着她们的生命故事,看口弦的故事在个体回忆中变得生动鲜活。 01 见证土地上的变迁 羌族口弦省级传承人 王泽兰 作为羌族口弦省级传承人的王泽兰,现在居住于北川羌族自治县青片乡西窝羌寨。其实从年她出生在上西窝的高山上后,她就与这片土地有着不可割裂的关系。她幼年与母亲独居,以做农活为生。王泽兰17岁的时候就被人提出入党。年,已经成为干部的王泽兰和她的丈夫,因他们上面有一家是“有成分的人”,上下过路不便于路过他们家,于是被“憋”下来了,一家迁居于西窝羌寨,加入集体开始了挣工分的生活。 虽然两母女住在山上,劳动任务也并不轻,但是村里的氛围很好,村里人还是有能在一起玩的时候,王泽兰也能融入到这个村子的温暖热闹的氛围中。谈起这段回忆,王泽兰说:“欸除了哪里结婚啊、过年的时候嘛,还是都在一起嘛,去耍。孩子家嘛,还是有点爱闹人嘛。你结了婚了过后,那时候集体天天都,男的就是定的三十个,你做不到那么多就要给你倒扣。女的呢就是二十八天,天天反正,就是我们这些带几个孩子的上,今天一满月,明天积分员就说明天我们又要在家劳动了,明天谁谁又满月了,哪里有时间去耍呢?” 虽然我们主要调研的是口弦,但是一说起村里大家一起玩的回忆,王泽兰先提到了一些同样也丰富了她早年记忆的其他羌族民俗,如刺绣、羌歌羌舞、婚嫁习俗等。说起羌歌,王泽兰回忆起那时唱山歌的美好时光: “一天做农活啊,做疲倦了啊,就都喜欢唱。但是还是有些(人)唱不了。就跟现在有些做针线扎花那些,就像我们这特别是还是有很少的有那么几个他扎不来。扎得好的呢,脑壳比较聪明的呢,要想怎样最巧。” 唱山歌的王泽兰 说到兴起,王泽兰又想起女儿也会做羌绣的事,便和我们说起了羌绣。“就是我的那个女儿,她在屋里的时候,就是画花,一天下来你要想在屋里做点什么嘛,纳的帽子啊、围腰子啊、鞋子啊,还有那个带带呀,鞋垫子啊,都弄得包起五花,都弄得喊她,哦后面那一天去了大半天哦,做什么呢,只有自己嘛,她就走艺术团去了嘛,那上面有个女的,算来她们也是姊妹,她们的老的是弟兄。她也会画,还有好几个在那的都会扎。”那时大家的衣服都是自己做的,直到现在,王泽兰身上那身具有羌族风情的衣服,也还是自己做的。 王泽兰女儿及其艺术团同事 而说到婚嫁习俗,王泽兰还是提到大家要在一起闹,一起唱歌一起跳舞,孩子们闹闹腾腾的,其乐融融。但是被问到我们主要要调研的对象——口弦——是否会在这样人多欢乐的场面中出现,王泽兰奶奶停顿了一下,说:“一般你想扯,你还是可以扯嘛。”她解释到,那个时候和现在不一样,会有集中去开晚会的固定活动,晚会主持节目的人叫到谁表演节目,就去表演。以前跳舞和现在也不一样,“现在这些舞都自编自演都,我们那时间跳的舞都,这些年那个电视里面放过,这下子他们都做不来了。这下子我给他们说了一下,他们就都会牵起,就跳。” 可见,口弦比起羌歌羌舞,在集体活动中略显失落。婚礼上不太扯口弦,取而代之的是对歌堂一说。 “嫁出去是坐在桌子边上对歌堂,它比如说插一朵花,搭几张桌子,唱歌。它开始是姑娘唱,先是新媳妇,新媳妇是你本人结婚,你就要做一个主动嘛,这哈唱了两边是引姑娘。你唱了,你唱好了,就把花移到我跟前,我唱了我又把花移到下一个人前面,就这样挨着挨着的,唱起走。还是热闹我们这儿。” 哭嫁更是不扯,大部分时间就是在干活累的时候,坐在大石头上扯口弦。口弦声小,一边走路一边扯,大家也听不到,所以都用更为响亮的方式——唱山歌取代了。 但是在王泽兰对过去的叙述中,口弦仍然有着不小的象征作用,那就是谈恋爱的时候男人要做口弦送给自己心仪的女人。被问到自己恋爱的时候是否收到,王泽兰奶奶说自己的丈夫那时雕不来口弦,而且在婚姻中父母的意见占了主要地位。女孩子主动找男孩子,是一件有点羞人的事,但是即使不能做口弦,男孩子还是能通过用山上的山核桃皮、玉米壳给女孩打草鞋来表达自己倾慕的爱意。 表达爱意还有另一种浪漫的方式,那就是对唱情歌。“对歌,有。他们那个昨年那个沙朗节,他们前面作准备工作,那些歌都多哦,男的(站)一侧,女的(站)一侧唱歌。”想想看,在美丽的田野间,或是清风吹过的绿色的山头,英姿勃发的男人在一侧,勤劳温柔的女人在一侧,用大家都能接受的方式诉说内心的爱意,是何等美妙又淳朴的事呢! 说起自己习得口弦的经过,王泽兰说自己是十来岁的时候从母亲那里习得口弦的,看着母亲扯,自己也模仿着,在屋子里随时对着扯口弦。在短暂的读书时日里,老师转身在黑板上写的时候,王泽兰就在下面扯,想来还有点对不起老师。说到这,王泽兰笑了。口弦音乐的传承向来如此,奶奶传给母亲,母亲传给女儿,女儿复又传给女儿的女儿。虽然由于各种因素,口弦在以前就略显失落,导致传承的火种虽微弱,然而倒也代代不绝。 王泽兰家的口弦 当时一起学的人不算多,也没有非遗这件事,大家也没有传承的意识。而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在这样自然的过程中慢慢形成了。说起和自己一起扯口弦的人,王泽兰说:“那个时间又没有谁来督促谁,就是喜欢扯嘛就跟着人家扯。这儿底下的嘛我的那个妹妹她也会扯。这还有一家昨天我们走的那上面,还有一家那个女的扯。她们那个往底下住嘛条件要好些嘛。我们这个只有怎样自己觉得好玩。” 但是,无论是群体还是个体,都是离不开政治的,与个体或群体的传承活动息息相关的口弦的传承,也受到了政治的影响。王泽兰也在早年看到了口弦“失传”的情况。“我看到58、59年失传了,那个时间破四旧立四新,那时什么都要喊。不提五几年的事了,就失传了。后面又抓起来了,看着看着呢,现在有专门抓文艺的。我们那个媳妇,他们在晚上他们那一批年轻人,就喜欢把灯打开,他们就跳舞,还可以自己自编自跳。这一种也是好的对吧。有时我还是真的看着有一点热心。”而文化大革命中,按照王泽兰的说法,口弦的情况是在“老一辈的心里”,就像现在的孩子读了书记在心里一样。“这个就叫说只要人在生命在,都保留在心里。”王泽兰说。 年的时候,王泽兰十八岁,在北川的文化馆里,当着馆长和其他人的面扯了口弦。那是她 次在青片乡以外的地方扯口弦。 时光流转,到了年前后,王泽兰成为了非遗传承人的。奶奶淡泊名利,与申遗有关的记忆已经不多,但却实打实地做过许多事情来传承口弦。她多次坐车翻过重重大山进行口弦音乐演出,增加口弦音乐的知名度,也多次去到北川县文化馆教授徒弟,毫无保留地传授自己吹奏口弦的技艺。 王泽兰介绍外出演出时照片 “这个嘛,我等于说蛮你们喜欢学的。我又这么大岁数了。有基础的喃还是等于就是我这个女子,学起也快,她得行。其他的还剩得远哦。有些是没得时间嘛有些她不耐心。学跳舞嘛都是学得快。这个扯口弦就是看起来简单,学的时候还是有点点难。”外面找她学口弦的人有好几个,来学的人大都是 十岁的年轻人,有些属于抽调来的文化馆、文化站的干部。她也去过文化馆教口弦,只要有人愿意学,她都可以教,但是由于口弦比较“抽象”,除有个别人模仿能力强,学得不错之外,其他人学的效果并不是很好。 王泽兰(左三)和其女儿(左一)、妹妹(左二)一起吹口弦 但是即便如此,王泽兰对于传承的未来仍然抱有信心。她认为,只要学口弦的人“开始就安心,还要用心,还要有耐心,要在内心表示这样一个态度”,就“学得会”,口弦就能传下去。这也是她对待口弦的态度。我们很好奇,做传承人那么久,她会不会在某一个时刻,突然有“一定要把这个东西传承下去”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呢? 王泽兰说了这样一段话: “是有这么一个想象嘛,你比如说人自己,上面都在费那么大的精力,天远地远地来了解这个,你自己嘛,作为传承人,是该要教给、传承到下一代嘛。 像往回子,我们这儿走个路都,我说脚扯到蛇了你都不晓得,现在我说走点路都是宽宽敞敞的、工工整整的,再没得啥子把蛇扯到脚底下。现在年轻人倒不晓得那些,他也没走过,我们才过了些艰难吃苦的哦。人老了嘞,说话都有点不行。 但是我前几年到现在晚上开晚会这些,只要我身体好,我就要扯口弦,扯了然后我就唱原汁原味的这儿的山歌。我就要给他们唱。这下子你说长的那些歌呢,我就有点点好像到 唱得就有点气息就不行了。你看我们这往年有一个老太婆,她死的时候也反正才七十几,唱了好多歌哦。我总觉得呢,自己呢,人家也看得起嘛,我也觉得欸,自己有这一种心态呢,知道你们那些要学的人呢那就来学。我有个孙女我不是把口弦给她,我问她学会了没有,她在教书,这下她说她把口弦都学得大意了,折断了嘞。我说那下一次再给你雕嘛。” 我们能够体会到,从年到现在,王泽兰经历了这片土地太多的变化。她能无比深刻地感受到这片土地的富饶与贫瘠,得到与失去,繁荣和失落,还有羌族文化的起落,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……无论是家里生活水平的变化,还是村子里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再次受到重视,都不只是王泽兰一人努力的结果,还有许许多多人付出了同样多的心血和感情。 “我说反正我们自己是羌族人,自己总要传承下去嘛。这一种,欸,人家天远地远的人来采访你啊,为了你这个不要失传嘛。”王泽兰 说。 屋外有几位穿羌族服饰的老人佝偻着走过。 -Tobecontinued-
|
转载请注明地址:http://www.dahuahuilana.com/dhhlsz/10102.html
- 上一篇文章: 孔子与兰花丨孔子好德寄情兰草
- 下一篇文章: 君子兰盆里长出好多小侧芽,这样去分株,成